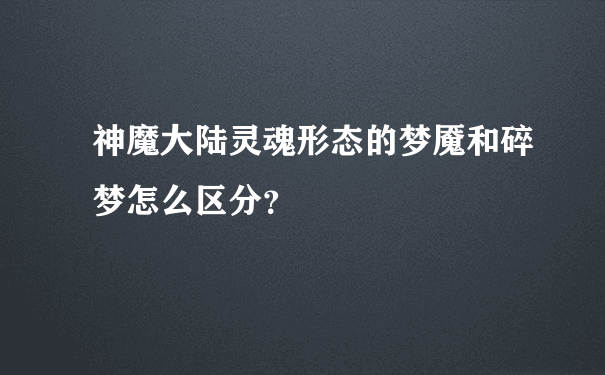如何看待「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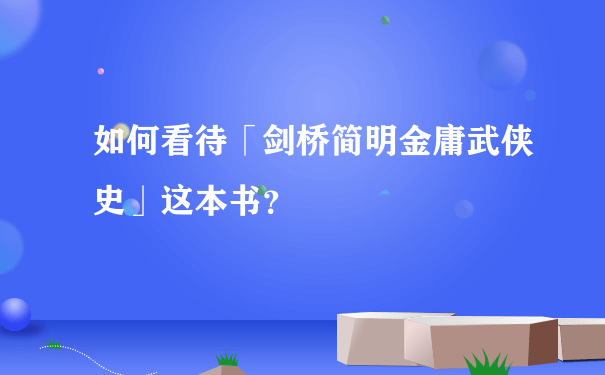
中国武术世界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上)——《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书评 作者 美国加利敦州克莱登大学 Dr. Rachel Chan 空耳(翻译) 华中师范大学 陈芝 本文发表在《读书》杂志 2013年第8期 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与研究,总是伴随着一个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尽管中国武侠史在故老的刻板印象里,是如同中国服装史、中国钱货史一般非常生僻的领域,但依然随着时代的演变而革故鼎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新武侠史”范式革命以来,涌现出无数优秀专著。他们的共同特征有:熟练使用心理史学的方式,以说故事的形式论述介绍中国历史,以独特的透视历史人文的视角,分析历史人物的人生兴趣与爱好、内心深处的忧虑与人性的基本内涵;采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大量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口头史,将之归纳整理还原历史真相等等。该史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查良镛博士、熊耀华博士、陈文统博士,他们共同奠定了当代中国武侠史研究的基础。 自向凯然博士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火烧红莲寺:湖南地下世界体系研究》开启中国武侠研究的先声以来,东方三博士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共同努力使得中国武侠史研究具有了世界级意义,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共同关注。其中,又以查良镛博士的研究最为突出也最有代表性,英国剑桥大学的萨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教授曾评价道:尽管其他两位博士的著作非常出彩,但自查良镛博士之后,所有学者的研究都是在为其所建立的体系查漏补缺,解决飘散在大厦上的那几朵挥之即去的乌云。 而Dr.Sean的新作则是在继承查良镛博士十四本不同方面的武侠史专著所建立的体系基础上,对中国武侠史进行一次系统性的论述。这种尝试前人早已有之,比如龚磬冬博士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努力,尽管龚磬东博士以文学史进行书写的方法最后失败了。 Dr.Sean的创见在于他缔造了一个新的范式,放弃了“新武侠史”革命以来的方法,反而采用政治学、社会学的方法,注重长时段的历史脉络和集团分析,对于故事本身的再现则是粗线条和外在视角的。这种引进现代社会科学的努力,尽管与先前范式相比使得著作的叙事显得极其枯燥乏味,然而却开始摆脱了故往研究里常见的粗浅的经验总结,在对社会发展的定性分析里抽象出一般规律,不再像龚磬东博士满足于对鸡毛碎片的小事津津乐道,而是试图从这一斑中窥探全豹,发现人与人互动的社会关系所折射出的历史本质。 在我看来,Dr.Sean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他对早期中国武术世界的研究和对明教教主张无忌之死的前尘往事以及这一故案背后的政治博弈所作出的精彩分析,将会被无数学者重视和引用,影响力必将超出中国武侠史这一狭小领域,吸引秦汉史和明清史学者的关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Dr.Sean对明清鼎革之季武术世界中的某些分析,与之前的篇章相比无疑是比较平庸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但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史学著作,Dr.Sean的问题意识作为全书的脉络,链接着中国自商朝诞生以来的三千七百年历史:中国武术为何会与之所寄身的国度一起衰落。在伴随着社会学分析的过程中,Dr.Sean将整个武侠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起源(史前——公元960年)、兴盛(个人主导的两宋时期960年——1279年)、由盛转衰(门派主导的元明时期1279年——1600年)、衰亡(帮会主导的晚明与清1600年——1911年)。在Dr.Sean看来,中国武术世界的兴衰与社会的开放程度息息相关,只有把握住社会发展的性质与结构,才能够理解武术世界,这与主流世界相伴相生的地下世界这么多年的光荣与梦想。 在全书的开篇,Dr.Sean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指出正是中西方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为什么中国会孕育出武术,以及西方会酝酿出后来取代武术荣光的科学:西方根深蒂固的主客体分离的对象化倾向,尤其自笛卡尔以来,灵魂和身体被当作本质上不同的实体,一切可被经验的事物,都被当作外在对象那样被观察、计算和控制,使其无法理解东方式的斯宾诺莎主义(Spinozism):意识和身体是同一个“实体”在不同属性上的体现,通过内省和自我调节对于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或方面都有与之对应的意识。因此,可以通过对意识本身的体验和把握而深入到身体性存在的基本方面。 对物我两分的主客体对立的执着,使得西方文明走上一条通往数目字与标准化,认为一切经验世界皆可以度量的现代科学的道路,更是缔造了搏击学、运动学这种通过对力的分析测算最优运动方式的学问。而中国由于坚持内省观念,使得人们无意愿去进行标准化尝试,这可从历代中国人模糊不清的数字概念可见一斑,因为内省的感受是很难与他人共享,并使之具有外在的实体性,自然无法推动人们将之度量,以精准的数字方便人们交流。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思维方式并非中国独家享有,一切不能主动孕育出现代社会的文明,也就是一切非西方文明都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强烈影响,而其可以追溯到人类学巫术时代各血亲部落的生活世界。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说法。 将意识与身体相统一的信念,使得中国人将古希腊人投向星空的视野转向自身,不断打磨身体挖掘内中隐而不显的潜能,漫长的文明与无间断的战争这吊诡的双生子又促使中国人有足够的时间与动力发展武学,并使之哲学化/神学化。在汤因比意义上的文明的早期阶段,交替的冲击与回应酿就了最早的粗糙尚未完善的武学以及日后的武术世界的雏形,尽管要在许多年后这个如今被我们耳熟能详的地下世界,才会瓜熟落地。这就像书中Dr.Sean揭示的中国文明的特质:强盛的王朝终将归于灭亡,但中国文明本身在不断的王朝更替中却能够展现自身的持续力量,甚至成为推动这种更替的动力。虽然,我更倾向于这是一个无尽的毅种循环。 第一个武学的繁荣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一个游侠时代,要归功于昔日强大的周王朝权威的毁灭。在镐京城被北方游牧民族侵占的灾难性事实面前,往昔万世一系的回忆是如此的无力。农耕民族与北方蛮族不间断的斗争,也塑造了日后中国武术世界的基本特质。但说来吊诡的是,正如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孕育了德意志民族文化上罕见的辉煌,在“春与秋”(Spring and Autumn)以及之后“诸国混战时代”(Warring——states period)四百年间,中国文化达到了它历史上的最高峰。日后的文明,不过都是在追忆那个琥珀色的黄金时代。 究其原因,在于竞争。数百个诸侯国家失去了天子权威的压制,不断兼并他国,试图掌握王室衰落后的权力真空。在撕开霍布斯的无知之幕/自然状态背后,是逐渐赤裸裸的达尔文丛林法则,强权即真理,知识即力量。生存逼迫君主在建立利维坦的过程中,大力培植一切繁衍利维坦的食料。原本稳固的自然秩序,在现实面前被另一种正当性取代,恰如刘仲敬博士所指出的: “在神性的历史中,毁灭秦宗权或张士诚不过消灭了一个机会主义团体(一群渴望宝贵自由的雇佣兵联盟,他们跟他们临时统治的地方和人民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跟赌徒愿赌服输没有区别;毁灭宗周或诸侯却是针对传统及合法性(由地方风俗民情长期酝酿产生的特色文化,统治者及其土地人民的有机性体现于礼乐和法统)的公然侮辱,是工具向价值的横暴挑衅。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对待这种挑衅,本身就是对文明价值的背叛。” 但同样是在这一片混乱当中,自由的种子在灰烬当中萌芽。战争撕开了封建农奴制的一个缝隙,演变成国家农奴制,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成新的依附关系。在这一变迁中,商人的地位因为君王们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得到空前提高,频繁的战争不能掩盖其商业贸易的增长。各国内部和平的实现以及君主专制的加强与封建采邑制度的消亡一体,下层的知识分子与武士慢慢取代昔日的贵族,成为战争与政治的主角,使得这一时期出现了平民社会的雏形。战争和商业的共同需要建立起庞大的国际交通网络,令人民、商人和下层武士及知识分子相对惬意地在各国间来往,孕育出最早的以覆盖中国本部的水道网络为基础的交通网络以及建立在这之上的社会领域——“江河与湖泊”(rivers and lakes)或“江湖”(rivakes),吹响了第一次游侠时代的号角。 而武术从其军事的母体中分离出来,不断摆脱世俗权力附庸的地位,与他们的主人一起开启自身的主体性,在“江湖”中穿梭,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一如Dr.Sean所说,“无论作为事实的叙述还是作为哲学隐喻,“江河与湖泊”都意味着自由空间,其特性来自于水的流动性。这一流动性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作为水的运动,使人们摆脱了地域性的血缘宗族社会的限制;第二,作为液体的水,不受凝固的政治权力的束缚。因此意味着一个既不被血缘家族关系所限定,也不被各级政府所约束的特殊领域。在形成任何自身的秩序之前,这一流动性的特征就是将这个在各国各地间不断往来的商人、知识分子和武士的交通领域和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区分开来。虽然大多数人只是临时性地进入这个领域,不久就复归故乡或是安身在君王的宫廷之中,但是也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些临时性的关系,其中一些逐渐凝固为固定持续的互动模式”。 虽然游侠在道德观上依然被私人情感和关系所左右,行事往往悖于日常道德,经济上因为无法独立而要依赖贵族阶层的供养,只是各国的分裂对峙才令他们可以较自由地四处旅行。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在人格上与君王是平起平坐,这是日后的江湖从未出现过的精神气质。游侠们不承认国家权威对自己的拘束,具有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正义观念,并自命为正义的裁判者和执行者,与统治者争夺这一原本被他们垄断的权柄。由于诸国的对峙带来政治统一体的分裂,各国君主与官僚机构不仅难以用强权消灭他们,甚至还被迫向他们表示尊重,以防止他们逃亡敌国与其联手对付自己。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扬的主体性,不禁让人想起尼采所宣扬的贵族精神对末人的反动,以及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末落》里,对被残酷的一战打光的欧美贵族阶层的怀念。在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依旧留存着这个时代的古风,直到勇武大帝诛杀游侠郭解为止,一如贝多芬弹奏的音符在不断笼罩的阴影里戛然而止。 尽管大一统的汉帝国可以说是一群游侠建立起来的政权,由于旧贵族的消灭,公元前二世纪的中国事实上已经变成一个平民社会,使游侠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社会基础。交通的便利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使得他们能够在帝国境内随意游荡,彼此结交,但帝国越来越无法容忍有人竟敢挑战利维坦的绝对主权。尤其在勇武大帝统治时期连年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所造成的政策转向,使得帝国政府就像二战时期的大英帝国,放弃了一直信奉的自由市场理念,祭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实施盐铁与酒类贸易的国有化和加征高额的商业税,打击商人,由政府统一进行分配和买卖。彼时繁荣的商业网络迅速萎缩,如果说不是消失了的话,商人们纷纷将商业资本转化为田产和农奴,汉帝国迅速向以统治集团为中心的农业国家回归。Dr.Sean指出,“这不仅以为这交通和食宿的成本大为增加,更意味着游侠所赖以活动的社会流动性也逐渐凝固——除了帝国本身之外,再无横跨整个帝国的体系。舟船往来的江湖世界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流民聚集的山林。武侠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经济史的一种表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二个游侠时代直到唐代才会出现,而真正的江湖和武术世界在北宋才会形成,这绝非偶然。” 在勇武大帝实施社会主义政策之后至隋王朝的700多年间,中国大地上都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宗法佃户制与从新的人身依附关系里挣脱的力量之间的博弈就此成为之后一两千年间中国大地的主旋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重新被国家农奴制取与其之反动所取代。当然,在这七百年间,宗教尤其是佛教而不是商业赋予了社会新的流动性,并直接孕育了现代武学。庞大的汉帝国灭亡后,道教与佛教在无尽战乱中的传播不仅提供了武术的哲学基础,更提供了武术的经济基础。对心灵与身体相统一的信念,在此时正式被系统化,佛教对于潜意识的精神结构和道教对于经脉的身体结构的概念之间的融合正是中国武学诞生的奥秘所在。诸如《黄帝内经》等文献以及禅定等手段的诞生,意味着我们现代观念中所定义认知的武学,只差实践中的临门一脚了。而政府、贵族以及民间对宗教的捐献使得大量的土地落入僧侣之手,这些不事生产者有充裕的精力去研究武学,在乱世面对觊觎者的威胁又使僧侣们有研究的迫切。 固然佛教试图独立或凌驾于帝国权威的努力不断告以失败,“但佛教最终通过融入和攫取江湖网络的方式,至少部分地脱离了帝国的控制。首先,佛教徒对于统治者的平等意识(他们曾宣布对于帝王不需要礼拜)、对于世俗生活的唾弃以及寺院经济的独立组织形式,使得他们在一切帝国臣民之中最不依赖于帝国政府的管理。在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各大寺院如同白纸上一个个不透明的黑点,虽然单独而言全都处于帝国的阴影下,但一旦江湖网络被建立起来,它们就成为其中重要的节点,为其提供稳定性的支持;另外,江湖的流动性也使得寺院能够彼此联络并相互庇护和应援,从而提供了对抗帝国的可能基础。事实上寺院不仅仅是僧侣的庇护所,也是在慈善的名义下,为一般的平信徒、商人、行吟诗人和知识分子提供暂时性落脚和居住的场所,这无疑有利于它汲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 日后大名鼎鼎的少林武学,便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虽然新生的少林武学其哲学基础以后世的眼光来看依然是粗糙的,要到唐王朝初期由于佛教道教在哲学与人体科学上的突飞猛进,吸纳了新兴的反意志主义观念之后,武学,或者更广义地说,把握人类心灵与身体之学术,才从宗教母体上脱落,在破除一切外在膜拜的心灵自省中,和武术修习结合起来。但在当时的中国,由达摩的弟子慧可开创的少林武学是真正的打遍天下无敌手,被无数人学习与模仿。所谓天下武功出少林,诚其谓也。 少林武学在中国的传播,就像无数条涓涓溪流汇聚在汪洋大海之中,融为一体,酝酿新的生命,一如同在无尽的分裂以后,这片大地的命运被新的帝国归于一统。唐帝国正式终结汉帝国灭亡后中国的分裂,在8世纪唐帝国归于鼎盛之际,游侠文化同时全面复兴。商业的发达和科举制度的推广,鼓励青年走出家乡闯荡四方,在帝国境内和境外,社会交往的网络再次活跃起来。在宗教运动中诞生的武学之火源源不断地向四面八方传播,摩尼教也在中国正式登场,谁也不能料到这个孱弱的小宗教,会如同日后的共产党,撼动整个中国。除了少林武学之外的其他宗派也开始出现,有些甚至活跃到清朝末年。武术世界日益壮大,并和主流社会网络有着密切的接触。不过,据有限的史料来看,武术家往往以个人的身份行走江湖,门派和帮会远远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社会组织。在唐帝国中衰后,相当一部分武术家依附于割据地方的军事势力,而这些势力之所以存在,又是由于唐时期门阀世家主宰地方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这些门阀世家其渊源,可以追溯至勇武大帝社会主义政策后的士族庄园经济。另一方面,诸如少林寺这样的宗教组织是武术家主要的培养机构和庇护所,军事和宗教两大载体依然是武术家的基本归宿。只有在下一个时代,武术家才能获得相对完全的自由。 被无数人迷恋向往的大唐盛世是相当短促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尚未完全兴起便早已草草结束。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唐帝国走向了它在8世纪的衰落和9世纪的毁灭。但这一政治局面促进了刺客与游侠文化的繁荣,已经发展了两个多世纪的新武术运动开始被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利用作为军事手段的补充,武术家们也反过来利用这一点,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领域拓展自己的势力和影响。这与公元前3世纪的情形,极其相似。而女性游侠作为一个群体,也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宗教延续了自己在武学上的影响力,在继承了慧可开创的少林武学基础上,道士吕岩(在中国民间被称为吕洞宾)针对臭名昭著的外丹学说,发明了内丹学说,这引起了武学史上的又一次革命,相对于外丹学说在金属熔炉中用通过化学反应炼制药品,内丹学说则认为应当将身体作为熔炉,人的体液作为药物,意念作为火焰进行“内在的”修炼,这进一步拓宽由慧可发扬光大的身心归为一体的学说,为中国的武者提供了新的理论方向。可以说,中国的武术世界到其彻底衰亡之时,都在遵循着吕岩所指引的道路前行。尽管吕岩所创立的门派“逍遥派”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在政治上一直没有作为,但他的武学理念就像当年的少林武学飞速地传播到帝国的各个地域的武者手中。 帝国自有其夕阳,重复轮回也好,更替动力也罢,庞大的帝国訇然倒塌,在历史的尘埃中粉碎地干干净净,仿佛就像几百年间大家共享一段春梦。中国被分裂为几十个互相争斗的独立小国,这一空前混乱的局面被称为“五个王朝与十个王国”(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do,907年——960年),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时代之一。但谁也没有料到历史的大变革就起于唐帝国的废墟之中,新生的力量固然孱弱,但当它抖动其细微的翅膀时,如果月球上存在观察者,想来一定会像胡风一般,激动地认为——“时间开始了”。 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化在天水一朝臻至巅峰,而内藤湖南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現在唐宋之际”;“唐代和宋代,在各方面的文化生活上都有变化”;“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重复着连绵的战争,唐帝国的毁灭加剧了这一现象。首当其冲地便是绵延千年的士族门阀的庄园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战争决定性地打断了贵族阶层的脊椎,原本能与皇权分庭抗礼的贵族阶层,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里彻底成为王权对抗官僚阶层的附庸。取代庄园经济的,则是由各地军阀领主大力扶持的工商业,许多失地农民因外力挣脱了庄园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作为无业游民成群结队地涌入那些尚未遭受战乱的城市当中,以此敲响了两宋平民社会的钟声。在这混乱无序时期,在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的夹缝,若干民众自发地组织发展起来,为了自保,少林拳等常见武术下渗至平民阶层,在民众中大规模扩散,而武术家往往成为这些组织的领袖与保护者,在混乱中出现的组织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未来几个世纪武术世界相当重要的角色,佼佼者比如丐帮。这一原始帮会的出现,意味着武术再也不是军人和僧侣们的禁脔,也不再是精英们的游戏。 Dr.Sean评价道,“在军事、宗教以及社会诸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武术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在唐代中后期出现了飞跃,形成了以佛教和道教哲学为理论基础的,禅定和内丹等修行方式为具体途径的高阶武学,并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的内战时代扩散到各个社会阶层。这一切都为一个新的时期做好了准备:当帝国的和平与繁荣再度降临后,一个崭新的武术世界就会出现了。”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江湖”即将登场了,时间真的开始了。
标签:金庸,武侠,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