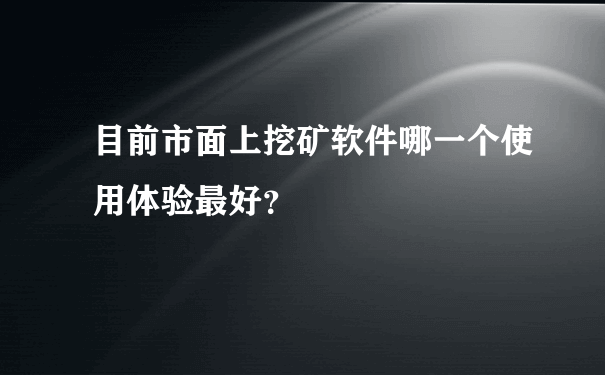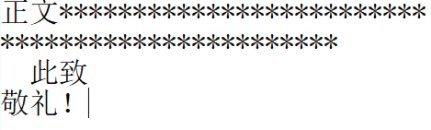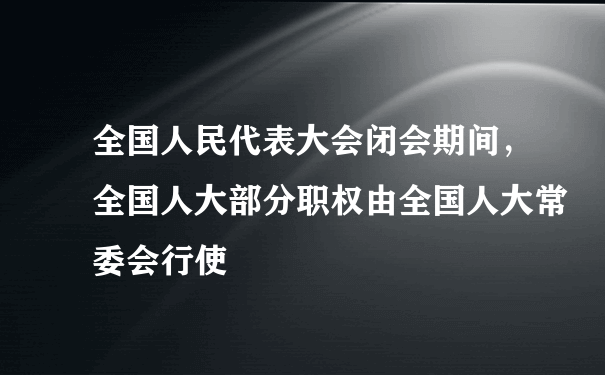如何理解左翼作家对胡秋原苏汶的批评?
张钊贻:《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 ——“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一、文章与背景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是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一篇重要文章,最初发表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的第1卷第5/6期合刊。原是给《文学月报》编辑周扬的一封公开信,内容是针对第4期芸生(邱九如)的讽刺长诗《汉奸的供状》。这首诗攻击胡秋原,但鲁迅认为诗中一些表达方式及其背后的思想意识很有问题。文章成为左翼文艺理论的经典之一始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张闻天和周扬看中文章的意义并非是“英雄所见略同”,与写作背景密切相关。
1931年12月始,胡秋原和苏汶(戴杜衡)批评左翼文坛,由此引发一场被称为“文艺自由”的论争。1932年11月,张闻天在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批评左翼文艺运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其实是响应中共试图改变党内关门主义状况的努力。当时,冯雪峰自然知道张闻天的意见,了解到“左联”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需要检讨和调整。据说,他看到《汉奸的供状》后向周扬提出批评,但周扬不接受,两人吵了一架。冯雪峰于是请鲁迅写文章,鲁迅“从公意”写成《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不料文章刊登后,立即招至四位党员盟员首甲(祝秀侠)、方萌(田汉)、郭冰若(钱杏邨)、丘东平联名发表文章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革命论”。冯雪峰请鲁迅写文章显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跟鲁迅与“左联”多数党员盟员一开始就存在的矛盾有直接关系。
为纠正“左联”关门主义,冯雪峰还于1933年1月发表两篇文章。《并非浪费的论争》由瞿秋白代笔,公开承认并纠正“左翼文坛”的“左倾宗派主义”,改变对“第三种人”的敌对语调并提出“联合”期望。瞿秋白也曾设法声援,留下手稿《鬼脸的辩护》,批评首甲等对鲁迅的攻击。这文章应该也是应冯雪峰要求而写,但不知何故没有发表。冯雪峰又介绍国外联合“同路人”的文章,把张闻天的文章稍加处理,将署名改成“科德”,转载于《世界文化》。经过一番努力,情况才在表面上得到改变。
二、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产生及遭遇,虽有中共试图改变关门主义的政策调整的原因,但基本上是鲁迅在“左联”的尴尬地位以及由此牵连到的“左联”内部矛盾集中表现在冯雪峰和周扬的对立。
两人的关系因《汉奸的供状》及《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产生对立。对《汉奸的供状》引发的矛盾,夏衍(沈端先)质疑冯雪峰为什么不传达张闻天的文章,但从首甲他们的文章中看,显然知道张闻天的批评。共产党时处秘密状态,冯雪峰不可能让周扬他们看张闻天的文章。尽管如此,冯雪峰还是告诉了周扬他们张闻天对“左联”关门主义的批评。按照常识和逻辑,冯雪峰能告诉胡秋原张闻天的批评,没有理由会向周扬他们保密。
陈早春和万家骥称,“有种种迹象表明”张闻天的文章是应冯要求而写。恐怕并非完全是事实。只要对照《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与《并非浪费的论争》就可发现,冯雪峰对胡秋原态度的明显变化,而这只能是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发表后的结果。如果看一下论战开始时代表“左联”的三篇文章会发现冯雪峰跟瞿秋白和周扬的一个差别:冯雪峰针对的只是胡秋原,而瞿秋白和周扬则把胡秋原跟苏汶置于同等的敌对地位。
据吴敏研究,周扬和冯雪峰的争吵,还有个人原因。但如果据此引申为冯雪峰和周扬都各有私心,争吵并非完全为公,因此“各打五十大板”则有欠公允。周扬对自己泄私愤直言不讳,但若认为冯雪峰因私人关系偏护苏汶,未免把他们当成市侩式的朋友关系。
如果我们把冯雪峰对苏汶的态度跟他与瞿秋白和周扬的不同联系起来,那冯雪峰“发动”这场论争的真正意图就更清楚了。很显然,苏汶是冯雪峰一直在争取的对象。当胡秋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评左翼文坛,提出作家应是“自由人”的观点,刺中苏汶这类有“进步”倾向作家动摇的要害原因,实际上是跟“左联”“争夺群众”,已经不是理论斗争的问题,冯雪峰自然要还击。但瞿秋白和周扬加入论战,把苏汶也当成抨击对象,要把苏汶推向敌方,实际上是给冯雪峰帮倒忙。《论“第三种人”》因此也显然是冯雪峰请鲁迅写的,而且冯还在文末加上苏汶“怎么办呢”一句,力图挽回瞿秋白和周扬批评所造成的损害。鲁迅的这篇文章跟张闻天的文章几乎同时发表,可以看成是冯雪峰纠正对“第三种人”批判偏差的部署。冯雪峰自己随后更写下《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对苏汶有所肯定,并批评了瞿秋白和周扬的错误。那么,张闻天的文章是否也是应冯雪峰的要求而写的呢?这样的说法好像张闻天没有思想主见,对冯雪峰言听计从,恐怕并不符合事实。
回到冯雪峰与周扬吵架的事情,其实与苏汶无关,关键是胡秋原。在此背景下,周扬发表专门针对胡秋原的《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无疑是特意向冯示威,向冯表示不买鲁迅的帐。如果周扬已经知道《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作者是谁,这算不算也是向张闻天和党中央示威?不好理解。也许,周扬会认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批评是冯雪峰“告状”的结果。由于里面体现了冯雪峰一贯的立场和态度,周扬可能认为中央偏听偏信,接受了冯雪峰个人的东西。也就是说,周扬也许不认为冯反对批判胡秋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图。这样的推测似乎还可以令人接受。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到底是“左联”上级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是否冯雪峰的东西其实都不是问题,作为党员的周扬到底也得接受,于是出现周扬与胡秋原同桌聚会的事情。周扬认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到了延安之后,应该跟张闻天谈过“左联”的事情,才终于明白冯雪峰当时代表党的意见。
冯雪峰作为周扬的上级,并刚刚帮助周扬恢复党组织关系,又让他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竟然不能使周扬接受自己的意见,而且还让周扬影响首甲等人公开抨击鲁迅。这些事情固然可以认为是“左联”关门主义深入人心,情况严重,但亦可以看到冯雪峰的领导能力似乎不无问题。如果周扬不认为冯雪峰的意见代表党的意见,那么他们之间的对立,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至于他们的矛盾,也许还是鲁迅看得准。据说,鲁迅多次说冯雪峰太老实,太认真,“斗不过他们”。如果鲁迅真的用上“斗”字,则他们两人和“左联”后来的变化和命运,也就不会令人感到诧异了。
三、鲁迅与冯雪峰等的差异
尽管鲁迅“从公意”写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支持冯雪峰和张闻天落实中共文艺政策,但在论争过程中,他的态度、观点和立场,实际上跟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并不完全一致。
鲁迅跟冯雪峰等的差异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关于鲁迅与胡秋原的问题,张宁指出,“革命文学”论战当初,胡秋原就支持过鲁迅,而鲁迅与胡秋原文艺上的观点其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不过鲁迅批评胡“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的谬误,尤其是从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来看,还是正确的。熟悉普列汉诺夫的胡秋原,只要考虑一下普氏著名的小册子《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就能理解“个人”受各种社会历史等等条件的制约,根本不可能完全“自由”。也许胡秋原说的文艺自由是另外的意思,但他没说清楚或没能力说清楚。如果鲁迅是在批评胡秋原,则他的批评的确点中胡秋原的一个理论要害。然而,当冯雪峰以“文学和批评的阶级任务”,瞿秋白以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要求来否定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鲁迅都没有声援,他在论争中根本没有针对更具体意义上的创作自由问题进行讨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很清楚的。鲁迅早已在辛亥革命前便清醒认识到以文学鼓动革命的限度,文学对社会改革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非常迂回曲折,根本在改变人的精神,而不在宣传与鼓动。而冯雪峰、瞿秋白和周扬却还在努力推动鼓吹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重复在鲁迅心目中已经破产的“革命文学”理论,即文学用作革命理论的“留声机”来推动革命,是否会令他有时光倒流的感慨?
他们的差异还有对“第三种人”的看法和态度。论争开始,苏汶观点鲜明,而冯雪峰、瞿秋白和周扬他们尽管用语和态度或稍有不同,但批判的锋芒也很清楚,就是文艺要不要为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问题。鲁迅对此不置一词,除了前述原因,也因为他们地位不同。
冯雪峰要争取苏汶他们,鲁迅虽写文章支持,其实是有保留的。论争结束后,鲁迅并没有停止对“第三种人”的批评。不过也必须指出,苏汶当初提出“第三种人”时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此后也有一个“潜在的演变过程”,并非始终如一。另外,虽然一般认为论战只持续了一年多,此后鲁迅固然没有停止批评,“左联”其他成员其实也没有停止批评。如果不包括鲁迅在内,“左联”对“第三种人”的批评其实一直延续到1935年底。不过其他人的批评着重文艺理论,跟鲁迅批评的焦点不同。
对于鲁迅继续批评“第三种人”的原因,研究者也做出一些解释。李旦初指出当时“血和泪”的历史背景影响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态度,黄悦接过这个观点,指出鲁迅跟胡秋原和苏汶在文学问题上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胡、苏求的是消解文学阶级斗争论,而鲁迅刚好相反,是要“把捉它”,“运用它”,在“血和泪”的环境进行反抗斗争,并以此“道德立场”继续对“第三种人”进行批评。他们所说并非没有道理,但还没有说清楚:鲁迅的是什么“道德立场”?对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鲁迅的《论“第三种人”》。
鲁迅在文中诚然也说明左翼文坛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但当冯雪峰以左翼文坛代表的姿态,承认过去的错误和要纠正存在的“宗派主义”时,鲁迅的表态却是如何面对左翼文坛并不完美的现实,一点儿都没有“回护左翼”或“替人文过”。他不但承认苏汶所指责的左翼作家中有人“左而不作”,还指出甚至有人化为“敌党的探子”;也不否定苏汶提出左翼评论家会批评“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认为可以想得更坏。当“左联”理论家在这些问题上跟苏汶纠缠争辩,鲁迅自然“失声”。然而,左翼文坛包括鲁迅在内,在重重压迫下仍然“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鲁迅跟党的“指导者”态度和步调不完全一致,但能一同前进,这正是“同路人”的特征。但“第三种人”不也是“同路人”吗?为什么鲁迅要批判他们呢?理由很简单,鲁迅并不认为他们是“同路人”。
鲁迅认为当时要超脱斗争的“第三种人”在现实中根本“做不成”。还有一类“第三种人”离“同路”更远,而鲁迅与一些共产党人对他们的不同态度更突出,如杨邨人等。
四、结束语:鲁迅与“第三种人”再认识的两个问题
文艺界自1949年以后,对“第三种人”和“自由人”论争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若按文艺界经验的认识来评价三十年代的人物和观点,则还需要结合当时才能中肯。
以苏汶“死抱着文学不放”但又惧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走狗”的心态论,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概很令人理解和同情,对鲁迅的批评进行重新思考也是很自然的事。在文艺问题上,鲁迅也许接近苏汶多于“指导者”,故论战初期“失声”,虽然对梁实秋批评的其中几点可以用到苏汶身上,但《论“第三种人”》批评的焦点并非左翼文坛的理论与政策,而是苏汶自身的矛盾。
苏汶的矛盾在于:想遵循“指导者”的方针策略,却又做不到。三十年代,上海文坛并非左翼独占,现实中存在不少并无政治色彩的刊物和作家,曾经“进步”的苏汶也只是参加了“左联”的一些活动便脱离了这个组织,并不在“指导者”辖下,完全可以无须按其“策略”写作,况且他还有一个圈子和同人刊物《现代》。但苏汶不想让“指导者”扣他“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一态度只能理解为他要珍惜自己左翼作家的身份。从冯雪峰的角度,苏汶这种既愿站在左翼并反感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作家是很好的争取对象,虽然他显然也遇到“宗派主义”的抵制。但问题是,苏汶很难争取,他两样都做不到:固然不会“左而不作”,但也作不出具备左翼特征的作品;既要保存左翼作家的标签,却要追求忠于艺术价值而又脱离当时斗争的“属于将来”的作品,也就违背一个左翼作家为大众进行现实斗争的基本理念和立场。“第三种人”对苏汶而言,不可能是一条出路。鲁迅所谓自拔头发离开地球的比喻,指出苏汶焦躁不安,不是别人摇头,而是自己做不成“第三种人”的缘故,其实是看得很准的。所以,苏汶的问题不全在文艺理论或左翼文坛路线政策。
对于“怎么办呢?”的问题,比较一下批评他的鲁迅会很有启发性。鲁迅通过翻译、培养作家、写杂文、支持大众语运动等来支持左翼文化事业。这些活动与鲁迅文艺运动“改造国民性”,与“五四”文学“为人生”,与文艺干预生活、参与社会斗争等左翼理念不但没有冲突,而且是一以贯之的。“左联”时期的鲁迅也没有改变自己去做政治政策的“喇叭”或“留声机”。当冯雪峰他们有意请鲁迅写一篇关于长征的小说,鲁迅没有写。他始终忠于自己,忠于现实。不过,他倒写了一篇更有思想深度的历史小说,也是政治寓言的《理水》。对于苏汶所害怕的扣帽子,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中,被扣的帽子可谓多矣,但他也从未“搁笔”,反而参与成立“左联”。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1935年,周作人借古讽今,引张岱评东林党虽多君子,但“窜入者”和“拥戴者”实多小人,影射“左联”及共产党祸国殃民。数月后,鲁迅在《“题未定”草》之九中几乎原封不动援引张岱的话,指出这类批评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实则反助小人张目”。鲁迅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并非不知道左翼文坛有“左而不作”而且善扣帽子的“小人”,也不是没有被扣过帽子,但他为了革命的远大利益,并不计较这些。只要能看到革命团体内还有“切切实实”“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君子”,还有希望,即使身处“横站”的处境,他仍会支持。这是个很难得的真正“同路人”的“道德立场”。如果没有这些不同,鲁迅这个“中间物”就会跟并非真正“同路”的“第三种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标签:胡秋原,苏汶,左翼